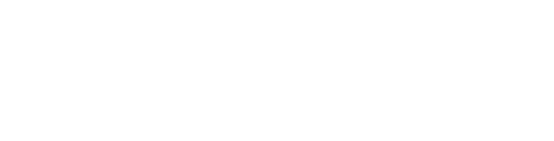原创 向天 局部观察
提到运动会比赛的“名场面”,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:菲律宾炸鱼队。
和这个一飞冲天的表情包。
实际上,菲律宾跳水队的名场面其实是出自2015年东南亚运动会的跳水现场,而飞天表情包的出处其实是1989年斯图加特世界体操锦标赛。
这还是有影像记录的时代,在影像资料少得可怜的早期奥运会赛场上,荒诞的事其实也一点都不少。
比如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的马拉松赛场上,赛事组织者詹姆斯·沙利文为了研究人类脱水状态的极限,规定40多公里的赛程只能补两次水。
美国选手洛茨跑完12公里后感到身体不适,毅然退赛搭上主办方的汽车,但在司机载他跑了17公里后,这哥们儿又觉得自己行了,并在下车走完剩下的7公里赛程后怒摘金牌。
后来洛茨的行径被人告发,随后完成比赛的希克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第一名,然而事后希克斯的教练却表示:“离终点还有7英里时,他已经跑不动了,很想退出比赛,我劝住了他,给他注射了两针,喝了杯法国白兰地……”
由于外国运动员太少,导致这届奥运会被硬生生办成了美利坚全运会,参赛运动员总共689人,美国就占了533 人;还包揽了96块金牌中的78枚。
这届奥运会之所以被称为“史上最糟糕”,还是因为组织者詹姆斯·沙利文,没错,就是那个不给人喝水的美洲大蠊,他脑洞大开,在奥运期间还搞了一个“人类学日”。
让菲律宾莫罗人、日本阿努伊人、巴哥塔尼亚人等来自亚非拉、没接受过相关训练的有色人种参与部分以田径类为主的奥运项目,以此彰显白人的基因优势。
之后主办方又安排这些有色人种参与包括扔泥巴、爬竿、射箭、扔重物,这些刻板印象里有色人种更擅长的比赛。优胜者没有奖牌,但是可以获得美国国旗一面。
如今,随着时代发展,越来越多有色人种站在了奥运冠军的领奖台上,当年连参赛资格都没有的小国也有了自己的奥运选手。
但是,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奥运会的格局,历届奥运基本都是五常带着几个“小弟”长期霸榜。
毕竟大国往往也是体育强国,经济不济或者人口基数太少的小国,往往只能充当奥运“气氛组”。
这些来自小国家的运动员,存在感最强的时刻,就是奥运开幕式上的入场。比如2018年参加平昌冬奥会的汤加选手,既是运动员也是旗手,一个人就是一个国家的代表团。
除此之外,还有安道尔、瓦努阿图、基里巴斯,阿鲁巴等国,基本上入场即谢幕。大家微信好友列表里的“安道尔人”,比历年安道尔奥运代表团的总参赛人数还要多。
这些小国运动员们从来没有站上过奥运领奖台,甚至连电视转播的画面都没有,毕竟,不是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像我们一样,坐在电视机前为自己的运动员加油呐喊。
因为奥运转播是一项花钱的技术活,首先需要奥林匹克官方转播公司在奥运场馆附近设立转播中心,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转播中心就占地8.5万平方米。
随后,各国转播媒体在媒体中心预定场地、筹备演播室等完成一系列的操作后,才能制作和传输比赛。赛事结束后,再把设备场地拆除运回自己的国家。这是一些小国无力承担的支出。
再加上奥运官方转播团队人手有限,全程拍完所有比赛是不可能的,只能捡着精彩的、观众基数大的那些比赛项目去拍。
各个项目的决赛肯定会拍,但初赛就不一定了,有明星选手或大国选手的初赛或许会拍,但安道尔和瓦努阿图之间的对决大概率是不会去拍的,除非他们那组同时有明星选手或大国选手,约等于上镜全靠蹭热度。
一个是播不起,一个是没得播。
但凡事皆有例外,比如在奥运赛程设置中,初赛时间较为靠前的游泳比赛,就是一些小国选手的露脸机会。
悉尼奥运会上,来自赤道几内亚的游泳选手穆桑巴尼,因为体力不支以及不怎么擅长游泳差点溺水。是的你看听错,穆桑巴尼是为了参加奥运会现学的游泳。
如果没有国际奥委会的资助和特批,只有几百万人口的赤道几内亚根本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。
甚至在获得奥运参赛资格后,政府还得通过广播向全国招募运动员,小半月只有几个人来报名,因为忙于生计的赤道几内亚人对奥运没啥概念,大学生穆桑巴尼就是其中一个报名者。
结果他还因为搞不懂规则,把原本想参加的50米自由泳,报成了100米自由泳,结果游完前半程,不会换气的穆桑巴尼就没蓝了。
不过,他坚持完赛的精神让那次比赛变得意义非凡,虽然取得了史上最烂的成绩,但也被奥委会评为了“奥运史上最伟大的倒数第一”。
这难忘的一幕,通过电视转播,被全球观众看见了。从那以后,奥运会游泳比赛便有了救生员。
穆桑巴尼之所以能被人们看到,并成为一种象征,是因为游泳比赛作为奥运大项,初赛在时间上和其他赛程冲突较少,转播压力不大,因此转播团队还愿意拍摄。
不过,更多的小国运动员往往没有这份幸运,许多比赛,尤其是小项目的初赛不会被转播。
他们或被埋没在海量的信息中,或当转播资源供不应求,需要进行取舍时,他们就被舍掉了。他们所在国的人民,通常也只能在开幕式上看到他们的身影。
在2010年广州亚运会上,伊拉克羽毛球国家队的唯一选手哈米德,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,只上场26分钟,没有队友,没有教练,而关于他的比赛网上只能搜到这样两张图,不免让人唏嘘。
这让我想起了第一位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刘长春。
1932年,身逢乱世的短跑运动员刘长春,在海上漂了三个星期后抵达洛杉矶,因体力不支,像如今的大多数小国选手一样在首轮就被淘汰出局。但他参赛本身这件事,就足以令当时内外交困中的国人激动不已。
当时的报纸写道:“我中华健儿,此次单刀赴会,万里关山,此刻国运艰难,愿诸君奋勇向前,愿来日我等后辈远离这般苦难! ”
1936年柏林奥运会,以李惠堂为代表的中国足球队,提前两个多月出发,沿东南亚一路踢了27场比赛,筹足路费才及时抵达德国。却由于一路征战,过于疲惫,在奥运赛场上,首轮即以0比2负于英国队。
在没有影像的时代里,国人只能通过报纸了解到他们。
新中国成立之后,国际赛事的传播有了新的形式。1957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上中国队迎战印尼队的那一天,先农坛体育场外,在高音喇叭下听实况转播的球迷黑压压一片。同时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向全国人民广播比赛的情况。
听足球,成了那个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里,人们对国足饱怀期盼的体现。这种对于国足发自肺腑的热情,一直持续到了今天,任凭风吹雨打,却历久弥新。
正因为我们也曾经历过体育弱国的阶段,我们也更能理解来自小国的运动员。
比如谈及被我们长期调侃的菲律宾跳水队,跳水名将吴敏霞就曾说过:他们没有好的训练场地,没有好的训练器材,甚至没有非常专业的教练员,往往都是靠自学。
训练之余,为了养家糊口,还要去做兼职。他们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实力,但他们仍然顶住压力,站在赛场上,这份勇气值得尊敬。
冬奥会的赛场上,也从不缺少来自小国的运动员,其中还有一些人来自从不下雪的热带国家。
比如汤加旗手皮塔,在16年里约奥运会以跆拳道选手身份参赛,为了参加平昌冬奥会现学的越野滑雪。
再比如在1988年的卡尔加里冬奥会上,来自牙买加的4位短跑选手参与了雪车项目。尽管他们在比赛中因翻车无法完赛拿了个倒数第一,但全场观众还是给了他们最热烈的掌声。
这次北京冬奥会上,通过最新的“云上转播”技术,小国运动员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。
数字化升级后的场馆,摄像机位更多、覆盖的比赛项目和环节更全。
即便是一轮游的小国运动员,也有了更多机会被自己的国民看到。
去年的东京夏季奥运会,因为“云上转播技术”,转播中心面积缩小了25%,现场减少了约27%的工作人员,转播内容却增加了30%,同时也为压缩转播成本提供了更大的空间。随着这项技术的发展,总有一天转播成本不再会成为小国运动员和祖国观众间的鸿沟。
1968年,墨西哥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颁奖仪式结束后,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田径选手阿赫瓦里才迈着简单包扎过的右腿,甩着已经脱臼的肩膀挪到了终点。
当记者问他,明知道已经不能获得名次,为什么还要坚持“跑”完全程时,他这样回答:“我的祖国把我从7000英里外送到这里,并不是让我开始比赛,而是让我完成比赛。”
从1896年至今,奥运百年的变迁史,也是一部影像科技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史。1904年的圣路易斯奥运会,总共只留下了31秒的影像资料,是现存最早的奥运现场短片。
体育的竞技性注定了不是每个人都能站在聚光灯下,但踏上奥运的赛场何尝不是一种高光?
转播成本的存在,决定了小国观众更难见证自家运动员的这一时刻,就像茫茫星海里不能被肉眼观测到的七等星。
好在,影像技术和云科技的进步,让阿赫瓦里们的光芒有机会照进自己的故乡。
- END -
原标题:《奥运会游泳运动员差一点在比赛中淹死》
阅读原文